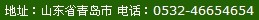|
哈巴罗夫斯克,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交界处东侧,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对于中国人而言,它有一个更加熟悉的名字:伯力城。 伯力城曾是中国达斡尔部落的世居地,也是明、清两代的固有领土。清朝后期,在《中俄瑷珲条约》(年)和《中俄北京条约》(年)签订后,伯力城归沙皇俄国所有,并以17世纪侵略黑龙江流域的俄国殖民军头目哈巴罗夫而得名“哈巴罗夫斯克”。 漫漫的江水,隔开中俄两国,为哈巴罗夫斯克这座边境小城的人口、历史和文化赋予多元的魅力。哈巴罗夫斯克的记忆不是单单由斯拉夫民族构成的,更是多民族共同记忆交织绘制而成的。百余年过去,哈巴罗夫斯克仍与中国保持着若即若离、一衣带水的关联。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重大事件多语种全媒体报道团在哈巴罗夫斯克游历期间,有幸采访到六位常驻哈市的华人华侨。让我们随着他们的讲述,翻开历史的书页,听听埋藏在这些远东游子们记忆深处的故事吧。 阿穆尔河落日 瓦洛佳-80岁-翻译 “我有两个祖国,都同样让我自豪” 初见瓦洛佳是在领馆门口的长椅上。他和他的太太清(化名)坐在阳光下与路过的人聊天。瓦洛佳长着一张亚洲面孔,却有一双湛蓝的眼睛。我犹豫半天,走上前问他:“请问您会说中文吗?”瓦洛佳露出不满的神色,嗤笑一声,说道:“当然,我是北京人呢。”见我面露尴尬,他又笑着说:“我是中俄混血,我母亲是俄罗斯人。” “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五十年了。哈巴罗夫斯克每一景一幕都很可以算是很熟悉了。我出生在西伯利亚,那里的风在冬天很冷。后来来哈巴工作。苏联解体前我在国际广播电台做翻译。广播电台你知道吗?”他脸上闪过一丝苦恼:“很多人一提到广播电台就觉得我们是做间谍工作,发秘密电报的。其实不是,我们就是播播新闻而已。后来苏联解体,有一段时间舆论管控很严,中央政府把地方的广播电台都关了。我们也就失业了。” “那生活会很困难吗?” “那时候俄语翻译供不应求,出去找工作总能找到活路,可以维持生活。”瓦洛佳沉默了很久,突然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人们总问我,更喜欢俄罗斯还是更喜欢中国。实际上,我一直觉得我有两个祖国,都同样让我自豪。像我们这样的人总是被人逼着做出选择,好像如果说两国都喜欢就是虚假。我挣扎了很久,不停奔波中俄之间,想要找到平衡,却发现唯一的答案其实很简单。我爱中国,也爱俄罗斯。而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两国的和平稳定相处。” 旁边的人突然插话道:“瓦洛佳可是哈市大名鼎鼎、受人尊重的翻译呢,他还曾经给很多大人物都做过活。” 瓦洛佳打断他:“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能像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一样做出决定性的贡献和改变。只能从自己能力范围可以触及的方向入手,尽一份力。” 清挽住他的手。他们相识于国际广播电台,结婚已经超过四十年。“他还当过红军呢,苏联时期全民征兵,瓦洛佳也去过。”她突然有些激动,拉住我们,“他真的为中俄交往做出很多努力。” 任何语言在此时都显得无力。我只能不断点头表示谢意。 “祝你们生活幸福美满,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哈巴罗夫斯科金顶教堂内 迅-85岁-倒货商人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迅长着一张很欧式的脸,高鼻梁,蓝眼睛,看起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俄罗斯人。他身边站着一位俄罗斯女士。他在瓦洛佳旁边,一言不发,似乎对我们说的毫无兴趣。 招待会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又一次遇到迅,四目相对有一点尴尬,我对他笑笑。他叫住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北大荒吗?”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他说的是北大,便笑着说:“当然知道啊,中国最好的学府呢。” 迅露出为难又诧异的笑。他说:“不是北大,哪能是北大呢?我们普通人怎能考得上北大。” 我有些尴尬,只能用赞美掩盖:“您的中文说得真好。” 谁知气氛变得更加尴尬,迅安静几秒,声音沉了沉。他说:“你知道吗?我是在佳木斯出生的。你知道佳木斯在哪里吗?” 我点点头。 “你知道知青吗?那些年在北大荒,从上海来的知青一批又一批。看到你们就又让我想起那个时候,一晃又是四五十年,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有些迷惑,“您什么时候来俄罗斯呢?”“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我被赶到北大荒,又从北大荒逃来哈巴。我在北大荒还做过老师呢。刚逃到俄罗斯的时候也没什么好做,只有倒货。和大老板一起。货物一箱一箱从北京拉到俄罗斯。情况好的时候,没运到莫斯科就全部卖完了。碰上苏联解体,卢布汇率不稳定。前一天才进五百美金的货,第二天就只值五分之一的价格了。难啊。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我感到绝望。俄罗斯人根本瞧不起我们,就叫我们黑毛猪,黑毛猪。走在路上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抢。” “我已经快八十五岁了,快乐或者不快乐也没什么重要的。而且你看看她。”他把他身边的俄罗斯女孩推到我面前,“她是我孙女,她甚至不会说中文。我想回去啊,可是我该怎么回去呢?” “她生活中所有都是用俄语进行的,学校,工作,没有人说中文。我倒是想教她啊,可是从何教起呢?”他长叹一口气,“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晚宴结束时,我对他说,我们要走了。 他眼里露出不舍,问我,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停顿很久,声音有一点哽咽。我说,我们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不回来了。”他喃喃自语。“我们相遇太晚了,那时你在和瓦洛佳说话时我就应该来和你聊天。” 他沉沉垂下头不说话,像一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只一味地坐在我旁边,有一点手足无措。 我感到很难过。我说,我们拥抱一个吧。 他愣了一愣,认真看着我,眼中突然充满了泪光。我听见一个哽咽又微弱的声音“谢谢你”。 ‘START’起跑线 苗云(化名)-55岁-服装生意老板 “30年后,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苗云一定是招待会上最耀眼的女性。她穿着富贵的祖母绿长裙,搭配着全套碧绿的玉饰。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到她旁边,阐明来意,她豪迈地笑着说:“你叫我苗姨就好了。” “我是90年代末期来俄罗斯的。一开始生意真是难做。资金就是大问题,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只能从倒购开始,回国批发服装,用不起火车就只能一点点从国内把货物拎过来。你知道‘拎包客’吗?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不过啊,你可不要小瞧拎包客,我认识的不少大老板都是从拎包开始的。一点点,一点点,像蚂蚁搬家一样,积攒多了就有了资金啊。有了资金就可以慢慢开始自己的公司。现在做生意就容易很多,可以贷款啊,但那时候连贷款都是没有的。还有就是安全问题,苏联刚解体时真是不安全,回家路上就总能看见有人躲在暗处,一不小心就会冲出来抢你。现在没有了,安全了很多。” “一开始来俄罗斯当然不好过,语言不通,那时候俄罗斯人总是高高在上,是看不起咱们的。总觉得前十年真是难,别人总觉得咱们是来这里逃荒的,做的事情也不体面,形成不了气候。后十年慢慢变好。一是因为咱们这一批蚂蚁搬家的人很多后来都成了大老板,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祖国越来越强大,现在走在路上也没人找我麻烦。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我们一家人都生活在哈巴。” “我退休了。我的女儿在哈巴开了一家酒店,儿子开了建筑场。所以我就放心地退回家里了。种种花,没事和朋友小聚一下。其实我最开始工作的时候目标就是为了养花,哪有女孩子不喜欢花的呢?三十年后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哈巴罗夫斯克街景 阿妍(化名)-23岁-留学生 “俄语翻译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 招待会上呈现出的不仅是中俄建交70周年来的风雨兼程,更是这70年来哈巴的众生众像。历史的痕迹,生意的往来,似乎都太沉重了一些,几次交往后便觉得筋疲力尽,心里涌起深深无力感。我决定逃离一小会,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四处观望,我找到了那个属于我的地方。走过去才发现还有另外三个窃窃私语的女生,亚洲面孔,礼服华丽,举着高脚酒杯,大而灵动的双眼透露出对这场招待会的兴奋与好奇。我小心地从人群中穿过朝她们走去,尝试着用破碎的俄语问:“你们会说中文吗?”三个女生犹豫了一会儿,齐齐点头:“我们从抚远来,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大学交换。” “感觉和这边有语言障碍吗?” 三个女生不好意思地笑道:“有的。我们从抚远来,才刚来一个月。我们从高中就开始学俄语,但说得还是不太好,俄语真是太难了。远东地区有很多东北来的留学生,因为离东北很近嘛,我们那从初中就可以选外语是读英语还是俄语。隔着一条黑龙江,商贸往来特别多,很多人宁肯不读英语也要读俄语。我就选了俄语,希望有一天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去莫斯科工作,然后回家乡当一个翻译。翻译这个工作可体面了。” “其实我觉得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真的挺友善的。虽然我们俄语说得不太好,但平常交流的时候,他们会不停鼓励我们,还夸我们讲得好。老师上课也会多用简单的语言,让我们也能听懂。至少这一个月来,所有俄罗斯人对我们都还是很友善的,没有碰到有歧视性的事件。” “我还是想回家去的。但是我也想看看,这个讲着我学了快十年语言的国家到底什么样。” 上外报道团采访当地居民 结语 我们在哈巴的第一天就看到了黑龙江。宽阔的水域在落日的余晖下金光闪闪。我们坐在江边,看着江水波浪平静,江对面熟悉的灯光点点,那是我们的,是瓦洛佳的,是迅的,是苗姨的,也是在俄千千万万华人华侨的故乡。他们大概是这段两个世界大国关系中感受最明显的人。历史的轨迹千变万化,洪流推着人们往前走,迫使他们做出选择,也给他们提供机遇。两国关系复杂,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的影响。从中苏关系蜜月期,到关系紧张,再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哈巴的华人华侨在工作、社会交往、生活等等方面最直接、最切身地体会了变化,体会到了变化带给他们的影响。 尽管这世界错综复杂、变化万千,有些事却从未变过。我们在哈巴的三天里,陆续遇到了很多华人。很多对话的细节虽然已经开始模糊,但是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是他们看到我们时久违,熟悉又带有怀念气味的笑容。从便利店门口叫住我们问:“你们是中国人吗?”的留学生到重要的大人物,这种感觉从来都没有变过:那对故乡深深的思念和怀念。共同话题来得很快,从城市聊到食品品牌,只要一句:“你也是中国人?”就可以激发出无限的联系。我想这就是,不管一个人走得再远再久,有些事,有些人是深深印在灵魂里,无法磨灭和遗忘的。 还有一件事一直在变化。那就是中俄大国关系。我一直觉得很幸运,在哈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以最直接的方式从普通人的角度探究这一深刻复杂的历史,政治难题。中俄关系的变化,在与这些华人的交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被看不起到越来越能够平等地相处,从矛盾到越来越能够找到合适双方的,互惠的,友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路上,我们总是听到各色各样的人讲:“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扫码中科出席第十届健康中国论坛大会初期白癞风可治愈吗
|
当前位置: 佳木斯市 >见闻感受俄罗斯我家住在江那头
时间:2020/1/12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鹰潭房价在全国城市排名算老几看完
- 下一篇文章: 应立即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猪肉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